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赵从旻
 【资料图】
【资料图】
1984年4月,华裔作家於梨华(1929-2020)女士在《中国书法》一书新版的序言中,形象地描述了她与华人艺术家、作家蒋彝(1903-1977)先生的一段交往,画面感很强。上世纪70年代,於梨华在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分校临时接任该校的书法课老师,前教职特别给了她一本《中国书法》(英文版)。於梨华阅后,感觉书的结构和内容太适合做大学生的书法入门教科书了,遂前去邀请有过一面之缘的作者、时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蒋彝先生亲自来做个演讲。年近七旬的蒋彝先生爽快地答应了,并婉言谢绝了专车接送,自己坐着长途灰狗(公共汽车),带着二十几支毛笔,拎着事先研磨好的墨汁,悠悠哉哉地就来上课了。课堂上,蒋彝先生边自如地演讲,边同步手书示范一个个中国字的形象来源。一钩一转,简单灵活的笔法就勾勒出一个女子和一把扫帚,示意着汉字的“妇”字。一个个地,课堂上他将“车”“燕”“好”等汉字也以笔墨一一手书演示,书画动作行云流水,如同舞者,每一步都在动的平衡中尽显风雅,极尽优美洒脱,令堂上一众学生惊叹不已。
上世纪三十年代,蒋彝先生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本用英文撰写的有关书法的艺术普及专著《中国书法》,为西方读者了解和理解东方艺术,直接开启了一扇大门。
蒋彝(1903-1977)
被忽略的中国作家
2019年6月29日,英国牛津市政府在蒋彝的牛津故居前挂上了一个蓝牌牌,以表彰他对英国文化艺术的贡献。这样的蓝牌,尽管英国街头很常见,但在英国900多个近现代名人故居蓝牌中,只有4%左右是为非白人族裔而设的,华人中目前有三位:孙中山、老舍、蒋彝。
牛津蒋彝故居被英国政府文物保护部门挂蓝牌。
在国内默默无名的华裔艺术家蒋彝,在国际上却是文化名人。他是英国皇家艺术学会的会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终身教授,也是用毛笔在宣纸上画熊猫的世界第一人。蒋彝曾极富想象力地在其作品《旧金山画记》里专门绘制了一幅经典的彩色插图:一只毛茸茸的中国熊猫漫步在联合广场上——画面倾注着自己浓浓的思乡之情,也对应和隐喻着自己的文化使者身份。
1937年,蒋彝因出版《湖区画记》一举成名,此后开启了他的“哑行者”系列画记。如今亚马逊英文网站上,蒋彝的多部英文作品依然在版在售:《中国画》《中国书法》《牛津画记》《伦敦画记》《爱丁堡画记》《波士顿画记》《纽约画记》《旧金山画记》《重访祖国》等等。它们成功地持续占领过英国、美国的各个畅销书榜,不断被重印再版,并广为各主流媒体推介评论。蒋彝也曾屡屡见诸英美各报章杂志、电台、电视台的采访,受邀各类文化艺术演讲,甚至个人纪录片的拍摄。在专业的书画展览和各类不同的书展上,其作品及本人也频频闪亮登场。而这些社会层面的成功,又为他的本职教学工作带来了良性促进。
《联合广场上的东方来客》,蒋彝画,图片选自《旧金山画记》。
蒋彝,字仲雅,又字重哑,笔名“哑行者”。1903年出生于江西九江一个儒雅殷实的中式家庭,他幼年聪慧灵气,受到父亲的艺术启蒙和深厚的人文伦理教育,视野不凡,信念持正。大家庭里祖辈父辈兄长的温情与父母相继离世后的孤寂交织,他形成了敏感又略带忧戚的个性。风起云涌的动荡时代下,长大成人的蒋彝先是考入东南大学化学系寻求科学救国,毕业后经历了一段乱世戎马生涯,又再走上为官之路,历任江西九江、安徽芜湖、当涂三地县长。
理政时期,蒋彝以年轻的心性和热情,追求现代性的理想中国。他的正义感与同理心,在现实面对军阀和官场的腐败昏聩,以及各种盘根错节的社会顽疾时,化作了痛恨、不齿与无奈。另一方面,中国城市与乡村的市井样貌、风俗人情,社会与人的不同层面的复杂关系,又让他在入世的实践体察中多了一份思考与认知判断,也成为他日后自名“哑行者”游历世界与撰写游记的基底与源头。
勾画一个没有国界的世界
1933年至1977年,44年间,蒋彝分阶段居留英美两国,并游历法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任教于不同的高等学府和文化艺术机构。观察、比对、融合不同的自然与文化,虽历经艰辛,他的视野却逐渐开阔,并不断积累、拓宽和更新着自我。
蒋彝绘画写作作品的出版思路动念于他为一部作品所配的插图。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英国公众开始对东方艺术产生兴趣,1934年,旅英戏剧家熊式一出版英语戏剧作品《王宝钏》,作品出版后红极一时。熊式一接续获投资并担纲编导上演了《王宝钏》,此剧在英国演出三年,盛况空前,合计演出多达九百余场,英国的玛丽皇后看了至少八场。这部剧后又至美国百老汇演出,熊式一还因此受到罗斯福总统的接见。《王宝钏》一书,徐悲鸿绘制了封面和卷首两幅图,蒋彝则绘制了内文里精美的12幅线描插图,这些插图视觉精致,唯美迷人,为该书增色不少。
《王宝钏》的一系列成功让蒋彝有了以写作出版作品为方向的意念和畅想。1935年,在一个官方中国艺术展即将举办的契机下,蒋彝获邀以中国艺术家的身份创作并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英文作品《中国画》(The Chinese Eye)。
蒋彝一生共计出版英文作品24部,其中“哑行者系列”画记12部。他用他的作品和东方笔墨做了大量直接的东西文化阐释,超越地域、种族、宗教、文化和政治的区隔与纷争,“勾画了一个没有国界的世界”。他一直在作品中表达着他“对生活和人类的欣赏”。
蒋彝并不是在书中做文人的凄哀婉转状,他的腹有诗书的咏志,辅之以视觉上的轻盈明快:简洁的线条勾勒、娟秀的书法、水墨的意境彩绘、插图中的那一抹翠绿与惊喜的一点红,流畅自然,韵味十足。
蒋彝的笔名“哑行者”,指的是到一个国家旅行,不懂它的语言,也不了解它的文化和民风民俗,只能用一种观光客的、他者的眼光沉默地观察。“异文化”的身份背后,蕴藏着丰沛独特的中国文化联想:牛津的番红花与中国的梅花,波士顿的龙虾与孔子的“君子远庖厨”,巴黎街头的杏花与庐山脚下的杏林,巴黎女性的软帽、胸衣、高跟鞋与中国近代三寸金莲的性别文化……他对中西诗歌、掌故趣事信手拈来,在静静地感受中,涌动着一波波怀乡之情。异域的气息,也在他的笔下鲜活。
《枫丹白露宫的鲤鱼》,蒋彝画,选自《巴黎画记》。
比同样用英语写作的林语堂更进一步的是,蒋彝不仅仅让西方读者领略了睿智的东方文化和他者思维,他的艺术和他的“画记”还现代性地展示、传播了东方文化中诗书画一体的独特魅力。他用中国的水墨艺术自如地表达着他的世界观和文学艺术观,将东方之美带给了世界。
蒋彝在国内并不那么广为人知的原因,应该是他去国前并不似林语堂在国内业已成名;此外,蒋彝是以英语作品出版成功的作家,他的读者和作品市场首先根植于海外,在还未及将其作品一一译成其母语时,蒋彝于第二次归国期间重疾复发,在未尽的《中国画记》和《中国艺术史》的创作中,叶落归根,永远地回到了庐山脚下。
1977年10月17日,蒋彝在北京去世。10月18日、19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降半旗致哀。11月15日,哥大副校长狄百瑞在校方举行的追悼会上缅怀这位中国学者、诗人、画家,称赞这位中国文化的国际使者把中国文化带到了纽约。
1977年11月28日,蒋彝的最后一部画记作品《重访祖国》在美出版,他的世界各地的亲朋好友陆续收到了赠书,每本都附了一张他生前的亲笔题签。
自上世纪80年代始,蒋彝的主要英文作品陆续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
《芬微湖里的鸭子》,蒋彝画,选自《波士顿画记》。
蒋彝的不凡
1938年元旦,蒋彝用毛笔写下了他的新年誓愿:
“我对任何事都不愿意平凡:我不愿意平凡而生,更不愿意平凡而死。总之,平凡二字是我的仇敌。我好胜,我爱名,我要出奇,我要立异,使世界人对我诧异,至少要对世界上有点贡献,而使世界永远的留恋着。”
蒋彝不甘平凡,他想做一个“真正把祖国的艺术美展现给世界的独一无二的中国人”。不过,他也认为他的作品“是一个中国人的独特表现,而不是全体中国人”。
蒋彝的不凡在于有着极强的结构思维和各种巧妙的“形式感”。
书法在中国是普及型的传统艺术,但让西方读者理解书法的意境和妙趣却并不容易。蒋彝的《中国书法》一书,既深入浅出地提炼了书法艺术的概要和精髓,又顺应了西方读者的需求和思维习惯,让他们在不懂汉字的前提下也能了解、感受和欣赏书法艺术的魅力。《中国画》和《中国书法》,以西方人可以理解的方式直观通俗地展示了中国文字、中国书法、中国画的根与脉,成功地将中国的书画艺术跨出了华语世界。
在“哑行者游记”系列的第一本《湖区画记》里,蒋彝证实了一个基本的艺术观念:英国的山水,如同中国的山水。他坚持用“中国的方式”表达他眼里的湖区景致,13幅水墨风景插图的笔墨轻重、缓急、枯湿不等,表现出画面的明暗、质地以及和景物的距离。这本他以第一版不收取版税的合作条件换来出版机会的书,最终成功地印行了九版。《伦敦画记》则以中国人的眼光,对伦敦包罗万象的日常,进行了“艺术和诗歌的重建”,他以中式“留白”的取舍方式来表现伦敦的浓雾,于日常生活中寻找美丽:“我对伦敦生活的种种方面了解越多,对人类、爱、美的信念愈发坚定、深刻。”
《牛津画记》英文版封面。
蒋彝在英国曾任职于世界上首家医学博物馆魏尔康历史医学博物馆中国分部,他独辟蹊径地将馆藏藏品以“与疾病死亡有关的民俗、人体的概念、中国药理学、医疗和外科实践”四大主题结构展陈,以此表现中国医学史的博大精深,所有展品一下子抖落历史的尘埃,重新布陈,变得生动有趣。
蒋彝的不凡也在于他穿透性的“他者”思维,他深谙编辑之道和读者心理。
他的画记作品,不是导游书,不是地理书,是中国人眼里的西方城市风物。英国媒体曾经评述蒋彝的作品:“有一种人性的内质,一种真实的有意识的生命,贯穿于无生命以及有生命的自然之中。中国画的这个最伟大的特点被运用到外国的背景,使我们原以为死亡枯萎的内容获得了生命,原以为苟延残喘的内容变得生机勃勃。”蒋彝用他的作品让各地的读者对自己的所在之地有一种“既陌生又似曾相识”的新感受。
蒋彝擅长以不同的写作角度贴合主题,且扬长避短,不落俗套。《战时小记》用了长信的叙述方式,将战时的创伤在生命与死亡、人与自然的东方哲理中抚平与消解;《北英画记》注重的是蒋彝访问北英地区时的心灵感受,他细腻地捕捉到一个个细节,在书的结尾列举了22个“快乐的瞬间”,构思奇特;《牛津画记》则更为侧重蒋彝个人的观察与思考,他并没有入读牛津的任何学院,却逛遍了牛津城,他将牛津那些卓著的本地特征,以“静物造像”般的质感和东方韵味糅合在了一起,此书多次再版,成为他的代表作品之一。
1940年,蒋彝创作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儿时琐忆》,重温了他的孩童时代。二十几万优美的文字,一百多幅市井小画,儿时的人、景、物、事,文图俱佳,情感丰沛。桃花源般的一段段记忆,万花筒般悠悠地流淌出一种老派的美丽与优雅,一种有规有矩、有神采有尊严的美。蒋彝认为,追求幸福美好的生活,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善举”。
《龙灯》,蒋彝画,图片选自《儿时琐忆》。
《儿时琐忆》为战乱动荡中的人们带来了治愈的温暖和精神的寄托,畅销英、美、加多国;1943年,蒋彝的《中国书法》一书也意外成为战时驻扎英国的美国士兵们的圣诞礼物,一时洛阳纸贵。艺术对心灵的关照和抚慰,无关国别与种族,这两本书后来也都转译中文版,今天读来依然令人新鲜和感动。
蒋彝的高光时刻是1956年的6月11日,他获邀在哈佛大学优等生联谊会发表演讲。他是受邀的第二个东方人,第一人是泰戈尔。蒋彝精心准备了一篇题为“中国画家”的演讲稿,既与自己的身份背景和人文理念相一致,又与美国思想家、文学家爱默生曾经的同台主题演讲“美国学者”(被誉为美国思想文化的独立宣言)相呼应。他巧妙地避开政治与历史的大题,从画家角度切入,认为历史上的中国画家必然是“学者、思想家、诗人、书法家的综合化身”,他们无不在追求“大我”的羽化,中国画家的艺术表现出的是“涵容、无私、无我、无时间性而且历久常新”。演讲中,他认为那些不朽的中国画,可以体悟出一种“温柔、和谐、满足、宁静”的感受,“宁静而均衡”的心智活动是中国人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先决条件。他还特别强调东西方文化的共通性:“我们当代人是文化交汇的产品,区分我们对突出我们并没有帮助。在学派和技术之下,埋藏着人类与大自然的诗性真理,那是所有文明的基础。需要获得认可的是人类文明,而不是国家文化。”这篇立论高远、论据丰富翔实、语言优美浪漫的演讲,可说是蒋彝艺术思想理论的结晶,字字珠玑。
蒋彝的遗憾
蒋彝的遗憾在于他的学术上的失落与挥之不去的乡愁。他的雄心壮志与异国现实生存的艰辛,艺术家的自由、敏感、热情的天性与自己背负的远在异乡的家庭责任,让他比常人多了一份矛盾中的压抑与苦涩。
蒋彝有着学术上未能有所成就的遗憾,有着对自己去政治化的立场的规避和约束,有着跨不过去的非母语写作的困境,有着在异国文化市场中谋生打拼的种种周旋、隐忍与迁就,更有着个人情感上长期的孤寂与欠缺。他一路漂泊,四海为家,在不断的进取成就和乡愁的离散之苦中度过了自己人生的大部分时光。
早年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蒋彝师从汉学家庄士敦(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他的艺术才华颇得个性不羁的庄士敦的赏识,在教职聘用和博士学位申请上,庄士敦都给予了蒋彝很大的帮助与支持。只争朝夕的蒋彝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同时,又抓住了出版机会,创作《中国书法》一书,他想一举多得地将《中国书法》一书替代他早先申报的“中国佛教”的博士研究方向。但此申请受到了另一位与庄士敦有不同理念的东方学院东亚系时任系主任的爱德华兹教授的反对,她认为蒋彝并没有潜心做学问研究,其作品及论文的英语语言润色也是依仗他人,不符合博士学位的制度标准和学术规范要求。最终蒋彝未能获得博士学位,也失去了续聘教职的资格。后来在汉学家、禅学专家、哈佛教授杨联升的鼓励下,蒋彝在美研究“中国禅诗”项目,想以此再度向伦敦大学申请博士学位,依然未有结果,这成了蒋彝的终身遗憾,也直接影响了他的教职身份的各种进阶。
蒋彝
在畅销书作家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与学者的专业学术成就之间,原本就存在着目标方向的对立冲突。以蒋彝的才华和能力,哪一条路对他而言都只是个取舍问题,而不是不能胜任。冥冥之中,蒋彝还是依从内心,由漂泊的不确定感和自己的个性优势出发,选择了自由的创作及相关教学为主要方向,虽然他终生都希望在学术上获得更高的肯定。蒋彝的独特和罕见的才华与能量,他的多种的“艺”和“技”,是其幸,也是其不幸,选择的可能性和事业的方向性多了,选择本身就已经非常考验他了。
蒋彝兴趣爱好广泛,对人类、自然、艺术、社会方方面面充满了天然本能的纯真之爱,加之他又对万事万物有自己独到的眼界和辨析能力,这种时常激情四溢的状态,如同他在《巴黎画记》里写道:“一开始写有关动物的文章,我发现很难停笔。”这样的旁逸斜出,时常沉浸其中的不能自拔,自然与专精、漫长,甚至无趣的理性严谨的学术研究之路有一定的距离。朋友们虽惊叹于蒋彝的才情、感性、敏锐、博学,以及诗书画文集一体的创作方式,时时感受其新颖,但这种无法归类的综合与独特,也失落缺损于可能耸入云天的一枝独秀,最终的结果自然也会被整体平均了。在现代世界的艺术圣地,蒋彝对同期在巴黎的华人艺术家方君璧与潘玉良也有着寂寥艳羡的心绪:“方有高雅的情趣,潘有高尚的事业,我既无情趣,亦无事业,除了涂鸦,涂鸦,还是涂鸦。”
蒋彝一直被乡愁和离散牵扯,他一生拥有过三个国籍:中国、英国、美国。他不断迁徙,一直处于“此心无所寄,他乡岂故乡”的心境,他在各地的居所仅是个工作和睡觉的地方。一个无定居的行者,自己就是一个世界,清苦。
蒋彝一生孤行海外,没有家人陪伴。他是个谦谦君子,教养极好。他珍惜友谊,对人慷慨大方,朋友间的支持和情谊是他的精神支撑:他与精神之友和合作伙伴英妮丝的绵长的友谊,他与学术严谨、个性较真直率的杨联升诚挚的互赏与共鸣,他与宽厚无私的历史学家白山毫无嫌隙的、松弛自然的朋友义气,他与徐悲鸿越洋之间深情的理解与相惜,还有他与熊式一、叶君健、萧乾、夏志清、韩素英、於梨华、赛珍珠夫妇等同代学人和艺术家的交集与各种合作……
徐悲鸿去世前不久,寄给蒋彝一寸黑白照片一张,照片后面用铅笔写着:“我病在床上,四个月没有割须,特奉仲雅兄留念。悲鸿 一九五三年六月。”足见二人深厚友谊。
在两性情感上,他也一直对自己“管得很严”。与英妮丝在重要作品上亦师亦友的事业合作关系,在情感的边界止步进一步的升华。直至年老,蒋彝疲惫了,也放松了,才将自己的感情交付于年轻的华裔科学家黄耀民,可惜他们之间三十五岁的年龄差异招致对方家人反对。最终,蒋彝只是把《日本画记》题献于她,以纪念这份未得圆满的感情。蒋彝在情感上的遗憾与苦楚,后来在与台湾和大陆的子女陆续建立联系后,才稍有安慰。
美国的著名艺术评论家,也是蒋彝的同事、好友亚瑟·丹托在分析日本俳句大师松尾芭蕉的游记作品时认为松尾芭蕉的旅行是“对艺术与宗教的朝圣”,这是他“体内焦躁不安之感的象征。他总是从感觉或是从对终结的希望出发,无意于回归,以寻求某种终极的逃离,到头来发现,逃离本身就是成就。”
蒋彝的西行是逃离,也是成就。
而松尾芭蕉本人对日本的同辈诗人也曾另有过一句忠告:“勿跟随大师们的脚步——要去追求他们所追求的。”
去追求他们所追求的,是我们今天了解和理解蒋彝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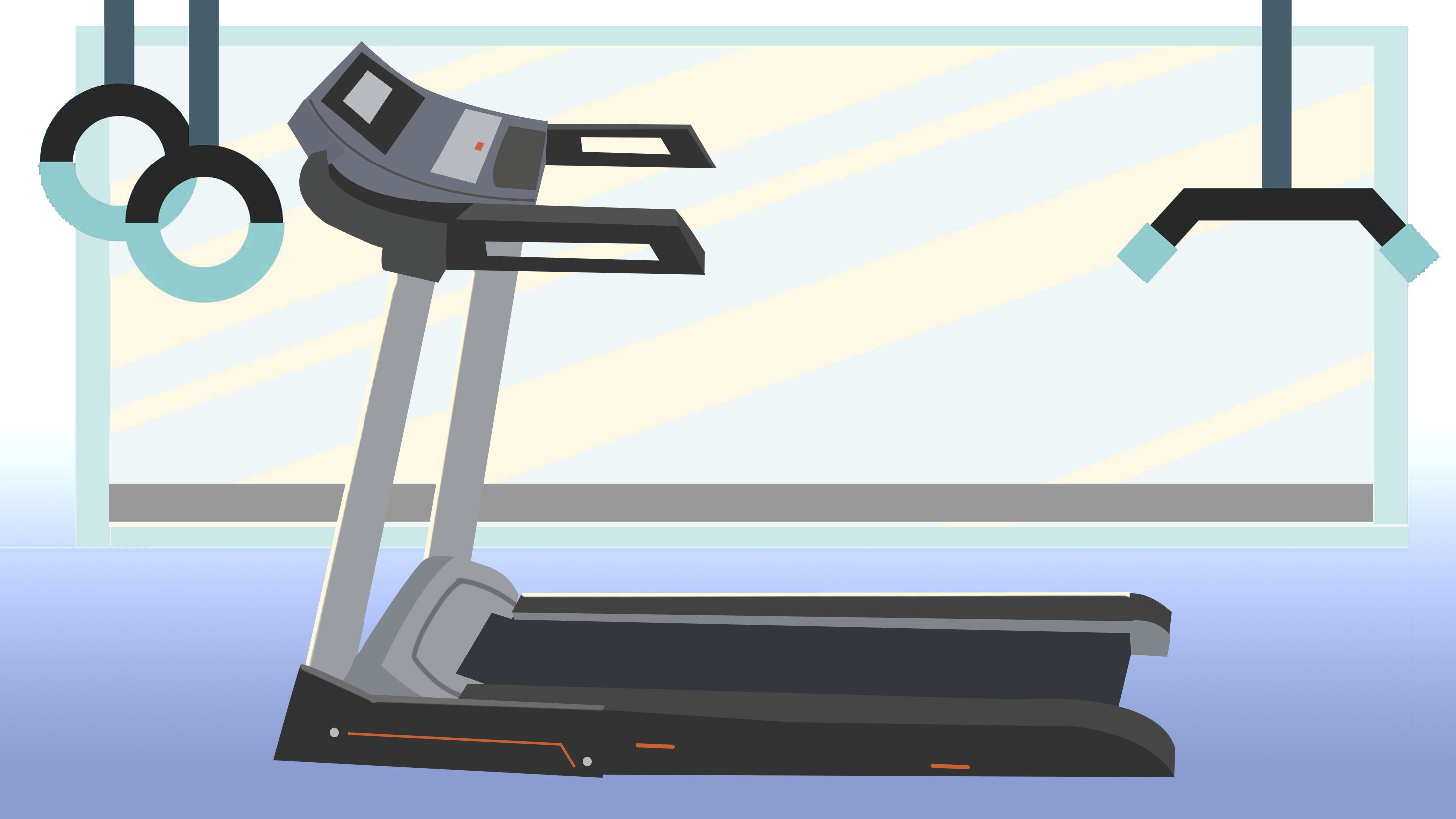

 厦门市投入超3000万元消费补
厦门市投入超3000万元消费补
 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出消费警示
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出消费警示
 故意隐瞒保险产品属性 销售
故意隐瞒保险产品属性 销售
 最新快讯!小米联合创始人洪
最新快讯!小米联合创始人洪
 快资讯丨苹果iPhone14/Pro系
快资讯丨苹果iPhone14/Pro系
 环球最新:哪吒汽车开启东盟
环球最新:哪吒汽车开启东盟
 22家贡嘎培优上市川企中 通
22家贡嘎培优上市川企中 通
 48小时点击排行
48小时点击排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