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对于我个人的艺术生涯来说,是极其特殊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演出了藏语版的《哈姆雷特》。
2021年5月7日和8日,由戏剧家濮存昕老师导演、上海戏剧学院西藏班表演的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汉、藏双语版在上海戏剧学院实验剧场首演,这部戏的剧本藏文翻译是由我和我的爱人格桑卓嘎担任的,那天我专门从拉萨前往上海观看,在东海之滨的大上海能够看到自己翻译的《哈姆雷特》演出,这在我的戏剧生涯中,是一件深感荣幸的事情。
《哈姆雷特》剧照
藏族有一句话,叫做“想吃糌粑的时候有人送来酸奶”,意思就是想要干件自己非常想干的事情时,意外有人提供了机会,我与这次的《哈姆雷特》相遇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我从小喜欢阅读,读莎士比亚就是很早的事情了。后来我自己从事戏剧创作,更是深入细致地读了莎士比亚全集。多次想把莎士比亚作品翻译成藏文,但是自己水平有限,况且曾经有著名学者和翻译大师把莎士比亚的一些作品翻译成藏文,有的甚至是直接从英文翻译过来的,所以,如果我扬言翻译莎士比亚,只能让人笑话。于是,这想法也不敢告诉别人。后来,我还是告诉了我妻子,她也喜欢阅读中外名著,藏、汉文都不错,她鼓励我做下去,并且她自己也想参与进来。于是我们两个悄悄地定了一个计划,就是等我们两个退休以后就翻译莎士比亚,每年翻译两部左右,用十七八年时间把莎士比亚全集全部翻完。当然,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梦想,我们并没有太在意,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翻译莎士比亚,很可能变成一个自娱自乐的事情,不可能得到出版和演出的机会。
藏文剧本中“生存还是毁灭”段落(译者手抄)
不料,机会确实来了。上海戏剧学院的杨佳老师在一次随意交谈中跟我提到过这个事情,我也好像顺口答应了,没太在意。2020年底,上海戏剧学院方面通过团里找到了我,把一本《哈姆雷特》剧本的电子版发给我,要我翻译成藏文,说这是上海戏剧学院藏族班的毕业大戏,要由濮存昕老师执导。当时,我很激动,也有些受宠若惊,没有提出任何条件,马上就答应下来。因为这正是前面我说的“想吃糌粑的时候,有人送来了酸奶”。所以,我在这里首先非常感谢濮存昕老师、杨佳老师,还有上戏的所有相关人员把我选做藏文翻译者。因为,他们使得我提前实现了我的一个梦想。
《哈姆雷特》藏汉语版海报
2021年的藏历新年刚过完,我就开始了翻译工作,那段时间我正在创作团里的年度重点大戏《老西藏》的剧本。白天忙剧本,晚上进行《哈姆雷特》翻译。我的妻子给予我很大帮助,我晚上翻译的东西,第二天她帮我整理、校对,所以她也是翻译者之一,大家在节目单上看到的译者之一的格桑卓嘎,就是她。大概用了二十多天的时间,按时向上海戏剧学院的佟姗姗老师交稿了。
说实话,真正翻译的时候压力确实很大,我在不断地问自己,我能胜任这个工作吗?万一翻译砸了怎么办?学生们说这个翻译太糟糕没法演怎么办?在拉萨演出,观众觉得翻译得怪怪的,听着别扭,吐槽了怎么办?那些在拉萨的大大小小的翻译专家批判了怎么办?……
去年在上海演出时,我说的是藏语演出的那天晚上,刚开始,我的确有些担心,因为这里毕竟是上海,不是拉萨,藏语演出还有人过来看吗?没想到,我们进剧场的时候已经座无虚席。演出开始了,两个掘墓人出来,开始用藏语对白,然后陆续国王、王后,哈姆雷特等重要人物出场,演员们在台上很自如地用藏语表演,舞台两边的屏幕上出现字幕。我偷偷地察看观众的反应。出乎意料,观众们看得专心致志,并没有出现我原先猜想的那种所有观众视线集中在字幕上,而不看演员表演的情况。更没有人交头接耳,悄悄议论。演出过程中,该鼓掌的地方大家鼓掌,该笑的地方大家欢笑,似乎观众们都能听懂藏语对白。
“上海的观众素质真好。”我暗自对自己说。
演出进行到半个小时以后,我似乎忘记了台上用的是藏语或者是汉语,只知道台上正在演出的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也似乎忘记了自己是这个戏的藏语翻译者,就像一个普通的观众一样完全陶醉在欣赏演出的喜悦之中。
演出一半,场灯亮了,中场休息。坐在旁边的自治区文化厅晋美旺措厅长对我说,“演得不错,藏语演出的效果比昨天的汉语版演出还好。”
我们交谈的时候,旁边坐着一位老先生,很眼熟。老先生主动过来跟我们交谈。
老先生问:“你们是西藏来的吗?”
“是的。”我们回答。
“我是上海译制厂的,我叫乔榛。”老先生自我介绍。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配音大师乔榛老师。我们忙毕恭毕敬地向他老人家问候。
乔榛老师说:“藏语很美,很有韵律感,我很喜欢。”我们表示感谢。
就在这时,上海戏剧学院的杨佳老师把我带到上海戏剧学院著名教授曹露生老师跟前,互相介绍后曹老师向我表示祝贺,说:“藏语特别好听,虽然我听不懂藏语,但是看得出来,你翻译得不错,台词很有韵律,很有音乐感,藏语演出更接近于莎士比亚原著。”
这让我更感到欣慰。他们对《哈姆雷特》的原著了如指掌,每句台词的内容非常熟悉,现在听的是一种语言的音乐美,韵律美。也许这就是欣赏台词的最高境界。
这之后好评不少,不论在上海演出,还是在拉萨演出,从普通观众到专家学者都对翻译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所以,我现在也敢谈一谈翻译的情况和感受。
莎士比亚对藏族文化的影响,是二十世纪下半时期才开始的。1981年,也是上海戏剧学院把莎翁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藏语版搬上舞台,影响非常大,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文艺界还在津津乐道那次的演出。第二次热潮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西藏资深翻译家旺多先生翻译和出版了《哈姆雷特》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全译本。可惜的是那两本译文没有得到演出,一是可能没有遇到好的机遇,另一个原因是由于这次的翻译是直接从英文原著原原本本一字不差地翻译,所以过于冗长,过于书面语化,不太适合搬上舞台。第三次热潮应该算是这次的《哈姆雷特》的演出了。作为这次的藏译者,自然感到非常荣幸。《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最负盛名的代表作,在内地汉语文化圈里,翻译和演出莎士比亚剧方面,已到了追求更好、更高、更美的阶段,但是藏文文化圈里面还处于填补空白期,所以,我觉得这次的《哈姆雷特》藏语版演出意义重大,甚至可以说,这次的翻译和演出的意义,远远超出演出本身的好坏。
《哈姆雷特》剧照
我们常说藏文化博大精深。这个博大精深,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藏民族处于非常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里,再加上藏民族本身是一个非常智慧的民族,所以创造了丰富独特的民族文化;另一方面,藏民族自古以来非常善于吸收外来文化,把很多别的民族的优秀文化吸收后融入自己的文化里,变成自己的文化。
借此机会,我还想再阐述一下这次藏语翻译的标准和特点。
首先、曹禺先生说:“剧本的翻译是以演出为目的的翻译”。莎士比亚的语言是古典文学的语言。也就是有强烈的书面语特点,藏语也有书面语和口语区分(虽然没有汉语的文言文和白话文差别那么大,但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如果太口语化,就会失去莎翁剧的语言风格,把莎士比亚的味道翻译不出来;如果太书面语化,演出时会比较别扭,演员背起来比较吃力,甚至很多观众也听不懂。我采用了口语和书面语相结合的方式。
其次、追求语言的韵律感。莎士比亚的戏剧是诗剧,虽然汉语的台词是散文体,但是读起来仍然很有韵律感。藏族文学最擅长用韵文表达。藏语言是一个非常优美的语言,非常适合写诗歌,而且词汇量极其丰富,表达方式也多种多样。藏族文学在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无数前辈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修辞手法,藏族文学史上出现过很多伟大诗人,藏族的传统诗歌都是韵文写成的。大家熟悉的仓央嘉措的诗歌,翻译出来也很美,但是若能读懂原文,那不知道有多美。因此,韵体的文学作品非常好译成藏文。
第三、莎士比亚作品里运用了大量的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而藏族文学自古以来也恰恰喜欢用修辞手法,有很多优美词汇和丰富的修辞手法可以挑选。藏族文学理论《明镜》里有丰富的修辞手法,光比喻就有三十二种明喻和二十种暗喻。所以,我翻译那些生动形象的比喻时非常自如。
第四、这次普通话与藏语同时排练,老舍先生说:“剧本翻译时不仅要看说了什么,还要看怎么说。”我曾经看过许多汉语演出的莎翁戏剧,包括濮存昕老师演的莎士比亚戏剧。所以,我翻译藏文的时候要看普通话版的语调和节奏是什么样子。所以,在这方面,我还要感谢一个人,就是这次的藏语台词指导宗吉老师,她把语言的节奏和语速把握得很好。
最后,我要感谢所有帮助和支持我的老师、领导,特别是感谢学生们的精彩表演。(责任编辑:孙小宁)

 两个品种LPR均与上月持平
两个品种LPR均与上月持平
 理财子公司如何走出差异化的
理财子公司如何走出差异化的
 四项标准聚焦于事故汽车维修
四项标准聚焦于事故汽车维修
 成都银行将于近期发行可转债
成都银行将于近期发行可转债
 金融机构存贷款稳步增长 楼
金融机构存贷款稳步增长 楼
 新车销售由增量市场逐步转向
新车销售由增量市场逐步转向
 健合2021全年营收115.5亿元
健合2021全年营收115.5亿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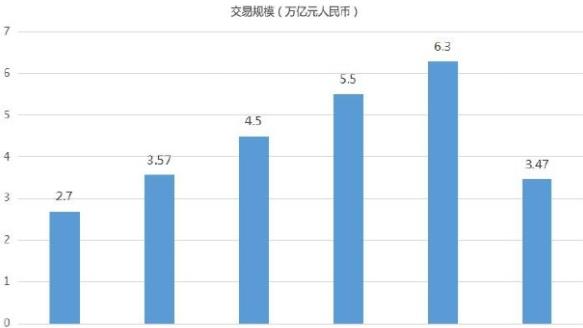 大盘反弹力度持续减弱 个股
大盘反弹力度持续减弱 个股
 48小时点击排行
48小时点击排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