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李兰芳
寻踪:问渠那得清如许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沿着什刹海西岸继续往北走,“潭面无风镜未磨”的浩渺光景渐生野趣,灵动了许多。缘岸葭苇一望无际,在这秋风微凉的清晨,却已染上了烟水苍苍,惹人竟起江南之思。
正当迷惘之际,我转过渌水亭,却被一片映日荷花怔住了!说起荷花,人们总津津乐道于圆明园的清宫名品,纷纷杂沓而往,一欲泛舟亲之赏之。我也时常思慕,何时才能一睹消夏。未料今日在积水潭的偶遇,眼前这片我从未听人提起,也还不知名字的荷塘,在我心中竟将往日所见都比了下去。
那接天荷叶重幽叠翠,在晨风中泛起了一层层绿色的涟漪。从碧绿中冒出的点点粉红,远远看去也绝无桃夭之姿。含苞打朵的每一个尖尖,都亭亭净植,竞相蹿出,等待着自己的生命怒放。而盛开的每一朵,都饱满挺括,硕大堪比牡丹,徜徉在这田田碧叶之上,看起来更是英姿飒爽,有如巾帼。我从未见过这么有力量的荷花!此番邂逅,真是如获至宝,流连忘返。
积水潭运海水门 李兰芳 摄
我沿着水边,试图寻找荷塘尽头,揭开这生机的秘密。路,似乎在花叶渐疏的东北角画上了终止符。而绿荷深处,似有人影攒动。原来,在荷叶荫蔽之下,有一道折向水中的浮桥。正在我为更接近这些巾帼英雄们而窃喜之际,又有一尊已被高高的苇丛掩没一半的塑像吸引了我。只见他目视荷塘天际,左手持卷,右指前伸,神情肃穆,如有所忧。在古人塑像“泛滥成灾”的今天,我起初很难将这尊塑像的主人公——郭守敬和这片荷塘奇观联想在一起。直到目睹了“运海水门”之前的流水活活,才明白了一些。此处水质之清澈,是北京城里少有的。成群的游鱼形迹迅疾,身姿矫健,虽无锦鲤之彩,却很容易被孩童们找到,引来阵阵高呼。桥下凫鸭也正成群争食,鱼儿们也都机警地避开了,迅速闪进了田田莲叶,藏身避祸。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观书有感二首》),这无限生机的秘密,原来就在这座水门之下!而这座水门,正是元代郭守敬的杰作。它已在这片荷塘,默默守护、滋养着北京城七百余年,成为了燕京文明的重要秘境。
文脉:我家水西涯 性本爱幽僻
这片秘境的渊源,也大抵要从郭守敬的大都治水说起。据《都水监事记》载,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郭守敬主持修通惠河。他从城西北昌平白浮山引水,流水绕瓮山泊后自西水门入城,汇为积水潭,形成了新的漕运粮道。流水继续向东南蜿蜒,汇入诸水,从南水门出,流入了唐宋时期旧的运粮河道,真正实现了运河的南北贯通,官私省便,惠泽万代。今日所见的“运海水门”,便与元时西水门位置大致相去不远。作为被元世祖称赞为“舳舻蔽水”的繁忙大码头,积水潭在当时的面积比现在的西海要大很多,以至于在人民心中渐有“海子”之称。
明代的海子大致还保留着元时风采,其水域之广阔有如江南云水,惠民之恩泽又传诵万代,借水利之便移居京城的南方士人也很容易对这带风物产生感情,流连咏叹,寄托兼济独善的抱负或情怀。
首先值得一提的,便是明代弘治年间官至内阁首辅的李东阳。李东阳祖籍长沙茶陵,因四代世居北京海子西岸,故又以“西涯”为号。在孝宗朝,他拓宽了言论通道,修《大明会典》,整顿财政,关心水利,时有“贤相”之誉。在宦官刘瑾专权之后,他请求致仕,却被迫蒙诟留下。但他并未与刘瑾同流合污,而是积极营救,扶持善类。《明史》高度称赞了他这种“非可以决去为高、远蹈为洁”,与家国同甘共辱的大臣气节。虽然李东阳的留守遭到了部分士人的讥讽,但他作为文学大家的地位是毫无疑义的。《明史》称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就连批评他“依阿刘瑾”的四库馆臣,也视之“为明代一大宗”。其创立的茶陵派,文法秦汉,诗法盛唐,主导了文坛近半个世纪。
李东阳的青壮年时期,是在海子西涯一带度过的。他的西涯书写,正记录了他人生最初的美好时光。其中著名的《西涯杂咏十二首》,便是以王维式的闲适笔调抒写了“我家水西涯,性本爱幽僻”(《赠彭民望三首》)的隐逸情结。这十二首诗,分别吟咏了海子、西山、响闸、慈恩寺、饮马池、杨柳湾、钟鼓楼、桔槔亭、稻田、莲池、菜园、广福观等西涯近地。在这里,李东阳时常流露出隐逸江湖之思。他喜欢遥望那海子上的点点渔舟,也喜欢遥想西山,像唐人一样,难以抵抗长安城外,终南山中,傍一湾幽溪,坐看白云而忘归的隐居诱惑。而饮马池、慈恩寺等地,则是他时常来饮马逃禅之所。西海北沿的荷花他也钟爱,尤其是在秋风乍起之时。菡萏香销,他也不禁咏叹,“秋风吹芰荷,西塘凉意早。独负寻芳期,苦被诗人恼”。其余如“月黑行人断,高楼钟漏稀”、“闲行看流水,随意满平田”、“老僧不坐禅,秋风看禾熟”等等诗句,都禅意悠远,充分流露了李东阳对这片祖居之地的热爱。
他希望,这份闲适与隐逸,能在未来的生活一直延续下去。毕竟,明初是禁止士大夫隐逸的。《明史·刑法》中规定,“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其罪至抄劄”。所以,能拥有一片水云居,时常看那忘事白鸥暮去朝来,对明朝士人来说是多么令人幸福的事情!所以,李东阳迁居西城之后也时常怀念这里。但他多次重游故地,却已是“悠悠二十年前事,都向春风梦里消”(《宿海子西涯旧邻》)、“月落空堂惊梦短,草青深院识春归”(《禫后述哀用祥韵四首》)的惨淡无情。踏入仕途之后,眼前之景,故园之乐,都已是“咫尺隔江海”,再也回不去了。
明弘治年间《甲申十同年图》,左一为李东阳。此图在清代年间为法式善所得
雅集 “魏阙之里”与“江湖之思”
作为一朝贤相与文坛宗主,李东阳在士人间备受拥戴。而乾嘉时期的蒙古诗人法式善堪称李东阳最忠实的“铁杆粉丝”。
他推崇李东阳“和平而冲邃”的性情,赞叹他“在官五十年,保全皆善类”(《题西涯先生像后》),为挽社稷而不惜冲逆宦党的刚毅品质。他对李东阳的活动作了深入细致的考索,为之校对诗集,编撰年谱,画像题诗。而他个人也十分关心国计民生,诸如水利农桑、治河开垦等事皆记于《陶庐杂录》当中。又别号“小西涯居士”,有《续西涯杂咏十二首》,追慕积水潭、汇通祠、什刹海、净业湖等昔日的西涯丽景。其一《积水潭》诗句“西山一夜雨,万柄荷花生”,借用王维《送梓州李使君》“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的构思,特别凸显了西涯作为赏荷胜地的特色。他在考证出李东阳的墓志之后,又时常在李东阳的生日六月初九这天邀约都中士人到西涯一带雅集。吟咏积水潭荷花,寄寓欢时易逝的感慨,也成为了此时重要的诗文话题。而法式善也在文人间声名鹊起,成为交游最广泛、最知名的重要盟主之一,时人也视之为“西涯后身”(朱珪语)。
洪亮吉是法式善西涯雅集的常客。比如,他写下的《游积水潭看荷花序》这篇精美骈文,便基本再现了彼时西涯雅集之盛,以及都中士人和李东阳一样存在的“魏阙”与“江湖”之间的心理矛盾。清中期积水潭似比元代有所萎缩,仅是“地居半坊,水积百顷”的水域。但这并不妨碍潭中风景的明秀依旧。在一片松榆杂植、水汽氤氲的烟波之中,鹭鸶翩跹、青蛙跃岸、鱼苗戏水、红楼隐隐、粉蝶翻飞。“荷盖蔽日,咸擎一枝;柳丝摇风,时揽数尺”,这样的景色同样楚楚动人,不减往昔。雅集的众人很快进入了兴致酣畅的状态。他们或饮碧筒之芳酒,或啜红鲤之鲜羹,或在林荫之下挥毫写图,或坐石隙之上联诗以遣兴。而水中倒影,也被比肩接踵的衣衫涂染成错磨斑驳的色块,随风荡漾,泛起褶皱的涟沦。林中虫鸣喓喓,花间水鸟簌簌飞过,和管弦一起奏响了“交响乐”,为雅集助兴。
然而,美好时光总是易逝的,今日的雅集之盛,朋比之欢,未必不会像王羲之笔下的兰亭集一样,是来日感慨悲欢离合、昔盛今衰的烦恼之源。是的,这种“既逝”的悲凉感,正是这群应邀雅集的南人们切实感受到的集体情绪。王芑(qǐ)孙在失约于法式善的雅集之后负责撰文追忆,同样流露出了这种易逝、易变的悲凉意绪。原因无他,正是因为“悲愉衰壮之感易于中,而烟云、卉木、暑寒、昏旦之候移于外”(《积水潭游记》)的自然定律。魏阙之里与江湖之思,在这里看似能合而为一,但从古至今都仍有待于人们自己去抉择。
按:清人完颜麟庆说,“净业湖在德胜门西,即积水潭,以北岸净业寺得名。”此为时人所绘《净业寿荷》之图。(清·完颜麟庆撰、汪春泉等绘《鸿雪因缘图记》,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年版)
结语
唐人赵师秀《野望》诗曰:“闲上山来看野水,忽于水底见青山。”这种“忽于”、“闲上”之所得,大抵是他最珍惜的瞬间,也是我们最美好的时光。由此我们不难懂得,那些赴约和未赴约的人们,他们在西海荷塘留下的既逝之叹,其实也都是对这种美好瞬间的铭记。也就是说,变化才是历史的永恒。我们不能再重复千年以前守株待兔的故事。不执着于某种结果,把握变化的瞬息,在瞬息中留住那份偶然而易逝的“有乐”,这份通达,才是古人传递给现代人的智慧。而西海荷塘年负盛情,洒然绽放,来这里的市人们似乎已经习惯驻足消夏、休憩流连的游赏模式,又或许,已不会在意葭苇丛中那尊塑像,以及这里的过往云烟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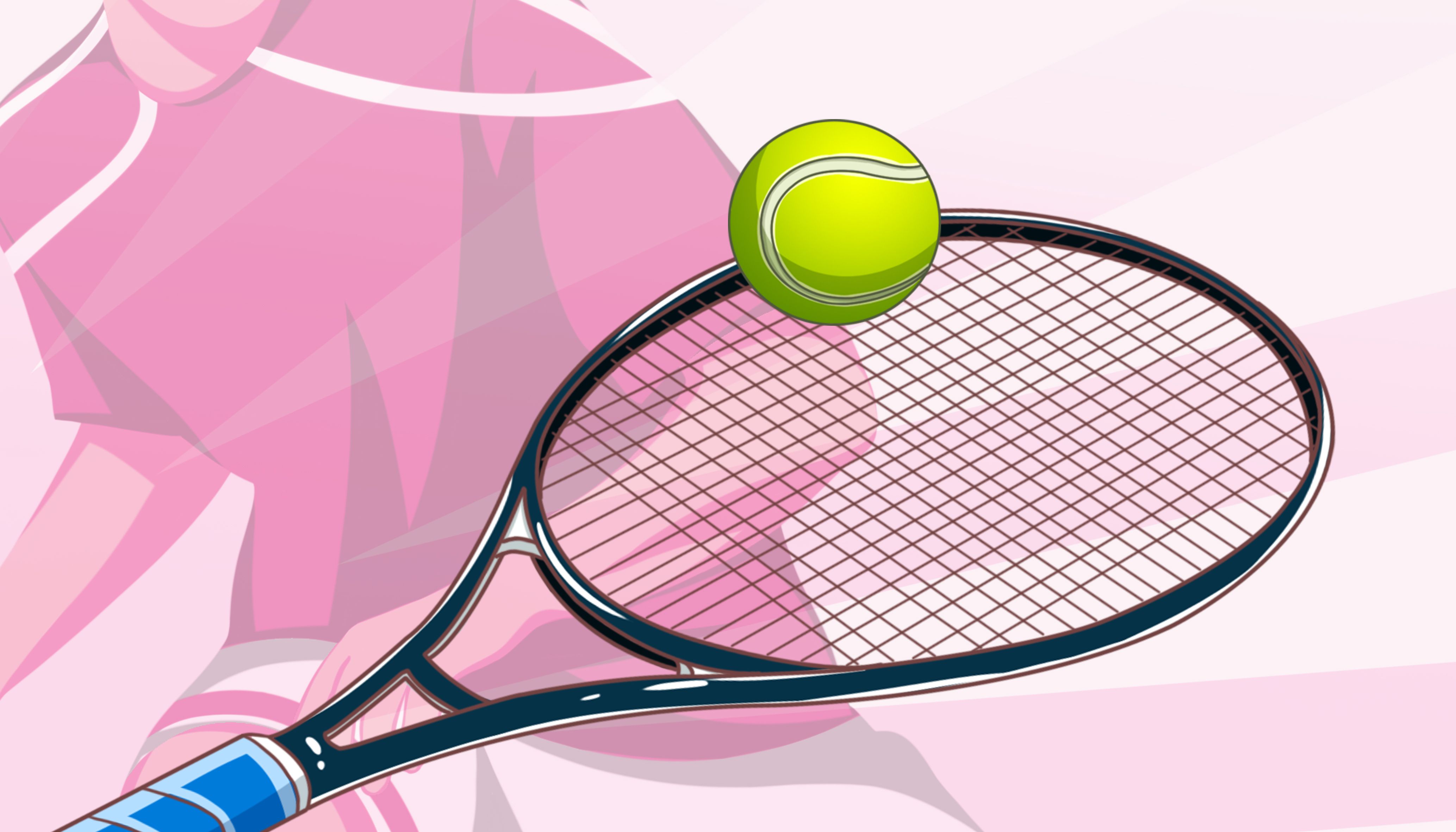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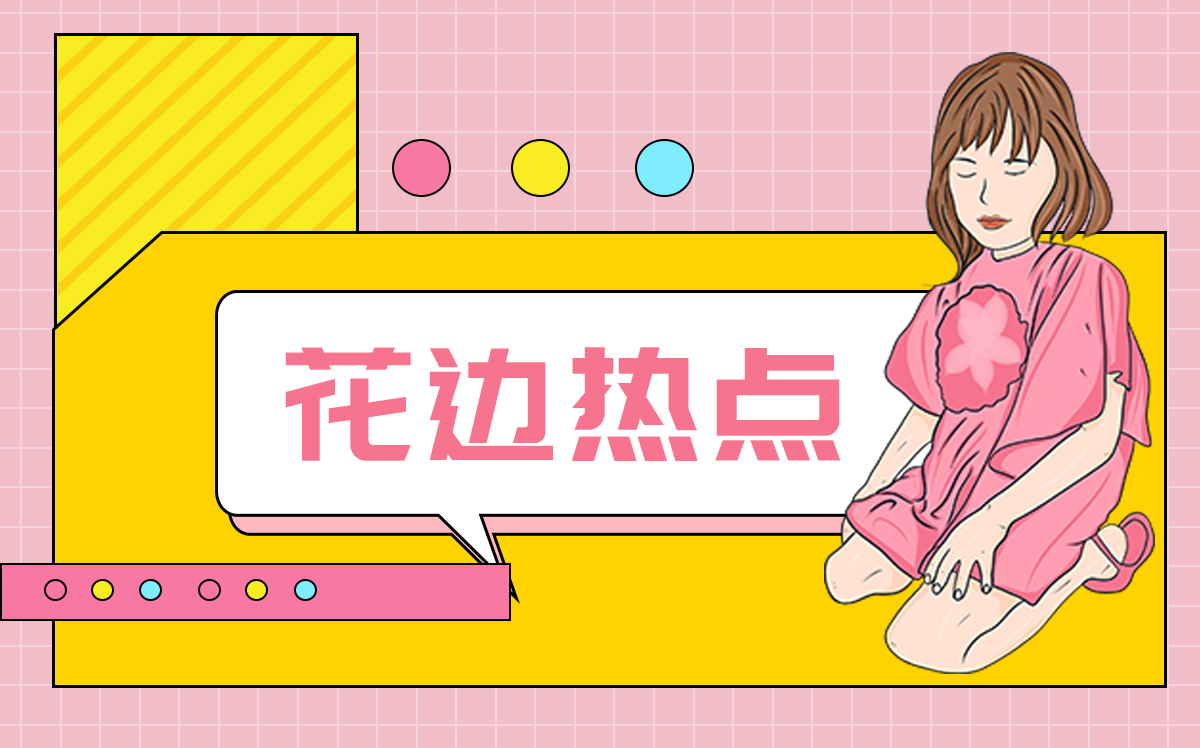

 高技术产业使用外资表现不俗
高技术产业使用外资表现不俗
 环球速看:信科移动:5G领军
环球速看:信科移动:5G领军
 大盘持续回调中个股跌多涨少
大盘持续回调中个股跌多涨少
 环球今日讯!网经社庄帅:数
环球今日讯!网经社庄帅:数
 环球百事通!财面儿|金地集
环球百事通!财面儿|金地集
 天天热讯:共计2366辆 起亚
天天热讯:共计2366辆 起亚
 新乳业布局鲜奶市场 未来将
新乳业布局鲜奶市场 未来将
 48小时点击排行
48小时点击排行
